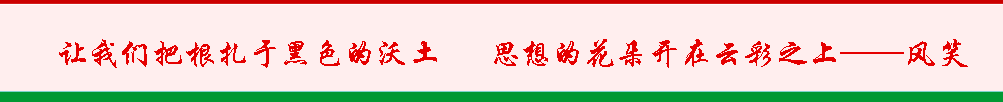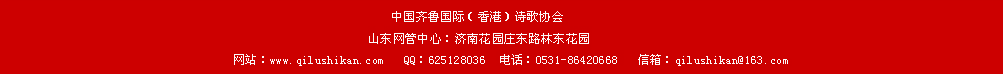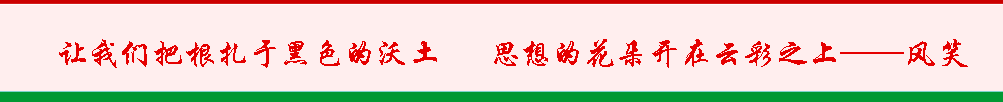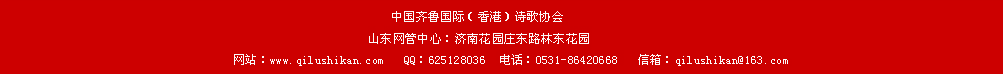夜,还是一样的夜。
有眨眼的星星,也有舞动的月光。
明晃晃、白亮亮的月的眼神,火炭一样燃烧着热情,在黑夜里肆无忌惮地挥洒着鬼魅的疯狂。
静静的夜里,只要你平下心来,就能听见月光“哧哧”燃烧的脆响。唯一值得遗憾的是,四下里缠绕着月儿的星星,看上去一派无动于衷的慵懒,落寞而疲惫地眨着眼睛,与月的激情形成极大的反差。
一样的屋内,爸爸妈妈不再背着我轻声地细语,也不再肩并肩、满世界地搜罗二人共同喜好的节目频道。
爸爸早已睡着啦。他那已有好些时日独居的卧房,已经为妈妈紧紧关闭了门窗。
清冷的月光下,客厅里的妈妈,还在“窸窣”地收拾一些爸爸允许由她带走的杂物。
妈妈把东西仔仔细细地分类,再板板正正地装好红色的皮箱。
那刺眼的红,如一团浓浓的血,冲撞着每一颗凝视它的心怀。
那口皮箱,是爸爸妈妈结婚时,姥爷、姥姥给妈妈陪嫁的,说是预示着爸妈今后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
如今,日子倒是火了,而人,却已不再是心心相印的那个人。
不知为什么,平日里一贯贪睡的我,此刻却睡意全无,猫狗一样蜷缩在妈妈身旁。直到腿蹲得又麻又涩,才从角落里拎了个小板凳出来,跟腚狗似的,妈妈收拾到哪儿,我就提溜了板凳跟到哪儿,而后悄无声息地坐在一旁。
这是个无论如何都让我高兴不起来的日子。因为翻过这个日子,也就是在即将揭开的明天,妈妈就要带了她的细软,永远地离开这个曾经风里雨里相依相伴的家!离开这个家肚子里盛放多年的忧伤、欢乐、嬉戏、缠绵和彷徨。
那床,还是妈妈搂我入眠时温馨弥漫的“一米八”宽的舒适大床;那布艺的沙发,摸上去似乎还有妈妈揽我入怀,刚刚坐过的温度;那“嗡嗡”作响的立柜式冰箱,依然塞满了符合我口味的一大堆形形色色的食品,然而,我已没了先前的那个胃口;那个四四方方蓝色塑料的储物箱,存放着齐齐整整、种类五花八门的玩具;往日里,调皮捣蛋的我,通常箱子一歪,“哗”地如数倾倒出来,身后便立时传来妈妈分贝渐起的没完没了的数落。而今,近在咫尺,我看都懒得去看它一眼,更别说去折腾了。
爸爸妈妈的协议中,白纸黑字地写着:“因感情不和自愿离婚,达成以下协议: 1、子女安排:婚生子……,归男方扶养,女方承担一半扶养费……”
自从偷偷看过这个协议后,我的心情就糟透了。
我明白,从今往后,我将长久地跟爸爸生活在一起,生活在没有妈妈的冰凉的日子里。
你不知道,没有妈妈,对我来说有多么的残酷!
为了这个,我曾不止一次地号啕大哭,并以此威胁。然而,犹如以卵击石,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。往日里一试便灵的杀手锏,如今却绵软得不再有力度。他们两个仿佛吃了秤砣铁了心似的,汤水油盐全然不进。
前段日子,爸爸妈妈闹得很凶,隐隐约约,我听明白了,是为了一个比妈妈小得很多的女人。
看得出,妈妈很受伤,泪水一遍遍滑过她清瘦的脸庞,背地里蜿蜒成一条名叫忧伤的河。
更加受伤的我,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,只能默默地递给妈妈一方小小的手帕,用来拭泪。与此同时,我的心,也像有刀片轻轻地划过,一阵紧似一阵地收缩着、疼痛着,却不再有人理会。
战火纷飞的当口,没人顾及我的感受。好多次,我在梦中绝望地哭着醒来,身体不住地哆嗦着,满头满脸都是惊恐的汗水。
八岁的我,已经上三年级,也算是个识文断字的人啦。一年级的时候,我就能声情并茂地通篇朗读《读者文摘》的刊首语,尽管其间免不了有三两处读错的地方。而今,我再也不会犯这些小儿科的低级错误啦,因为,我早已学会了查字典,还有上网查资料。遇到不会念的字,不理解的词,可以大大方方名正言顺地去请教“字典、网络”老师。
自从那薄薄的一纸协议,被我窥探明白之后,我的笑容就不再,情趣也不再。整天价,我不是把自己闷在教室里,就是闷在自家的屋子里,任如画般精致的往事,在眼前一幅幅流淌。其中有一幅最惹眼:爸爸妈妈开心地笑着,把年幼的我拥在他们中间,我的一条胖乎乎的腿,搭在爸爸的腿上,而另一条,则搭在妈妈温热的手心。我想,那张照片,该有个无比温馨的名字,叫幸福……
瞅着话语骤减、时常泪水涟涟的我,妈妈的心,被毒蜂蜇过一下似的,痛啦。毕竟,我就是妈妈(我是妈妈心头上割下的一块肉),妈妈就是我(我们本就是一人切割而成,从理论上讲,合起来,必定还是一个完整无缺健康无损的人)。
都说母子的心,是相通的。我能体会得到妈妈难忍的疼痛,如同妈妈也知道我的疼痛……
妈妈开始绞尽脑汁,耐心地做我的思想工作。说我大可不必担心,虽然爸妈将不再生活在一起,但对我来说,结果都是一样的。爸爸依然是爸爸,妈妈也依然是妈妈,什么都不会改变,更谈不上失去。
未来的岁月,我依然幸福地拥有一个爱我爱到骨子里的爸爸,也依然拥有一个疼我疼到心肝上的妈妈。妈妈还说,倘若不是她有病、不便长时间地和我厮守在一起,打死她,她也不会同意把我留下的。她说,她比我更想我们拥抱在一起的那些充满欢乐的日日夜夜。
“宝贝,别担心,妈妈给你安排了最完美的生活。跟随爸爸,以他的经济实力,对你的将来会更好一些。”妈妈说,她会经常回来看我的。漆黑的夜里,会有通体雪白的小兔子绒毛玩具,陪我一起沉入甜美的梦境(比如:跟妈妈做游戏;同小木偶,那个叫“匹诺曹”的家伙,一起学马戏;像“奥特曼”那样奋勇杀敌……)。
除了单位出差,妈妈这还是头一回离开这个家,而且还离开得那么长久,说白了,似乎根本就没有归期。
平心而论,对于这一点,我是打心眼里老大不高兴的。非但不高兴,隐约中,还有一丝酸涩的东西正一缕一缕地往上爬,如笨重的蜗牛在驮物,虽然动作缓慢,却阴云般地积聚,如同暴风雨来临前的天幕。
晨曦里,站在门口目送妈妈的我,脑海似被决绝地掏空了,里面空荡荡迷蒙蒙的一片,如雾正酣,模糊得我理不出一点儿头绪。
有一阵凉爽的风,调皮地挠了我一下,使我豁然清醒:什么蜗牛驮物?!分明是堆积起来的疼痛嘛,或者说,是无边无际的恐惧。
我一直弄不明白,为什么那些看似成熟、龙睛虎眼、头脑好端端的大人,一旦触碰到感情,就像中了邪、魔鬼缠身似的,明明是死去活来地相爱过的,并且为了延续这份没齿难忘的真爱,还不畏艰辛地将足足八斤的我,费时八卦地生产下来,神明一样地供奉着,期望成为他们爱情永恒的信物。可为什么,会陡然发展到如此田地?
从有记忆的那天起,夹杂在黑夜里的我,愣是没离开过妈妈温暖如春的怀抱。妈妈抚摸我的既纤细又柔软的手,火舌一样舔着我小猫般弓起的脊背,滑滑的,暖暖的。在妈妈的臂弯里,我是安徒生笔下熠熠生辉的王子,帅气、富足而幸福绵延……
好多琅琅上口的催眠曲,都是妈妈安抚我睡觉时,我自然而然跟着妈妈的哼唱学会的。
你听,妈妈的声音多么清脆,如冰击玉壶、瓷器落地般婉转;妈妈的声音多么甜美,如琼脂甘露,缓缓注入我幼小的心田:“月儿明风儿静/树叶遮窗棱啊/蛐蛐儿叫铮铮/好比那琴弦儿声啊/琴声儿轻调儿动听/摇篮轻摆动啊/娘的宝贝闭上眼睛/睡了那个睡在梦中啊……小宝宝睡梦中/飞上了天空啊/骑上那个月啊/骑上那颗星/宇宙任飞行啊/娘的宝宝立下大志/去攀那个科学高峰……”
像个魔术大法师,一首名为《月儿明 风儿静》的摇篮曲,一遍遍地被妈妈轻言细语地哼唱,在一个个静得大气都不敢出的夜里。
而我,则像被施了魔法似的,慢慢地,慢慢地闭上了眼睛。
催眠曲响起之前,妈妈还时常不厌其烦地给我讲故事。邻居家的阿姨,常常听见我陡然爆出的稚嫩、清脆的笑声,那笑,银铃一般,在静静的夜里萦绕、回响,就连燃烧的月亮都停止了舞动……
一直到我上学,顽皮的我,门门功课全优,学习非常突出。早早的,自己便能读懂许多大人的东西,还学会了查字典,辩解其意。
但让我始终闹不明白的是,那些大人,既然曾经背水一战、真心地相爱过,为什么还要像天边浮游的云一样,一点儿一点儿地从爱人的眼皮底下刻意溜走呢?
可我,是飘不走的那朵。我的心,已随着那溜走的云,玻璃一样,碎成了七零八落的模样,那玻璃样的东西,一落地,砸下来,就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忧伤。
永远忘不了,那天妈妈临走前,一步三回望我的揪心模样,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“楚楚可怜”。
在挪出十几米远的时候,妈妈忽然小跑着折回来,温柔地伏下身子,将呆愣如木的我,一把搂进怀里。
这是一种母亲才有的温暖,我感觉到了那种暖暖的温度。我知道,我将深深地失去它,在不远的将来。这种预感不止一次地光顾过我的大脑,还有我幼小的心田。但是,面对这种失去,我小小的身躯伫立在那里,一动不动,甚至没有泪水流下来。
我知道,我原本滂沱的泪,已在随之而去的无数个悲痛不已夜晚的梦里,大片地倾尽、枯竭,如不可再生的资源一样,不复归来。
躲在母亲的暖怀里,我感觉到了,那是熟悉的妈妈的手,在一下又一下充满怜惜关爱地抚摸着我小小的脊背。那纤弱的、柔若无骨的手,簇簇火舌一样,“噼啪”作响、强而有力地灼烧,让我放松而温暖。
自打生下来,我就是个幸福无比、沉在蜜水里淹着泡着的孩子。
我永远忘不了,那一个个像乌云一样慢慢退去的黑夜。
黑夜里,每一个酣畅的美梦,都诞生在妈妈温暖如月光的怀抱。那时,我是多么地幸福,又是多么地富足!
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故事,你听说过吧?那是我在妈妈臂弯里听过的,好几次,我都紧张得不得了,脊背挺得僵直,眼睛里燃烧着焦灼,就连小小的胖乎乎的手心里,都攥出了细密的汗水。
是妈妈,亲昵地浅笑着,用柔若无骨的纤纤玉手,一次又一次抚摸着我的脊背,抚摸着我软软的绸缎般细滑的胸脯,爬上我毛茸茸的头发,跌落在我高高撅起的小屁股上。
在大面积无休止的抚摸中,我不再害怕,将圆圆的头,安然地枕上妈妈的臂弯;将小小的柔软的身体,缩进妈妈的怀里,紧紧依偎着,带着一丝不经风浪的满足,微笑着甜甜睡去,嘴巴微张着,嵌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。
说实话,妈妈离我而去,我是打心眼里不高兴的,可以说,是一万个不乐意。因为,我再也不能屁颠屁颠地跟在妈妈的身后,撒娇耍赖,或者是使性子。
曾经司空见惯的亲昵,将蜕变成一种无形的奢望。
整个下午,我都一声不吭,老老实实地坐在妈妈旁边的小板凳上,看妈妈匆匆收拾大大小小的东西。我看见妈妈从写字台的玻璃板下拿了一张照片放进钱夹,我知道,那是我和她的合影,是妈妈最喜欢的。照片上的我,小鸟依人般坐在妈妈的怀里,笑得如花灿烂。照片里的妈妈很年轻,也很甜美。那时的爸爸很爱很爱她,没完没了地跟她没话找话,逗她开心。而今,事过境迁,往日的一切都像凭空飞翔的大鸟,“轰”地一声,折断了巨大的翅膀,翻卷着惨痛坠下,隐去了踪影。
另一个如花巧笑的女人,代替了妈妈在爸爸心中的位置。而妈妈,已花期不再。家庭的琐碎,刀斧一样在她脸上凿下了鲜明的痕迹。只从她看我时依然明媚的眼神,方能寻到一点模糊的往昔。
下雨了吗?我感觉有什么东西滴落在我的发上,我细细的颈上,然后,还有一滴,碰着了我小小的手背。
我感到了妈妈肩头些微的抖动。这种抖动像传感器一样波及到了我。于是,我也跟着抖动起来,并且幅度越来越大。
有东西在妈妈的眼里闪过。她轻轻松开揽我的手,把低着的头,一点儿一点儿从胳膊上滑过,而后,绽开一个明净的笑,朝向我。接着,恋恋不舍地朝我挥挥手,毅然地别转身去……
不知为什么,瞅着妈妈慢慢缩小成点的背影,我的心,竟倏地有了一种诀别的感觉。那一瞬,我跳跃着飞奔出去,挣脱了爸爸宽大有力手掌的撕拽,离弦的箭一般,冲向已不见了妈妈踪影的那个太阳升起的方向,拼尽全力:“妈妈……”
天高海阔,我撕裂的呐喊充满了依恋,充满了无奈,更充满了无助和绝望。仿佛世界的末日已经跑步来到我面前,我恐惧地一遍遍地抗拒着、呼喊着,泪水汹涌而下,恣肆地越过小小的面颊,浸湿了妈妈为我新添的霓裳。那些我曾经深深喜爱的新衣裳,猛然间失去了缤纷的诱惑力,没了一点占据心田的分量。它们统统地,对我不再重要。真的,不再重要。因为,我已没有了爱我疼我的妈妈。我小小的世界,黑色的魔法师已狰狞地撒下了一张遍布天地的大网……
黑夜已乌云一样铺天盖地笼罩下来,像个密闭的玻璃瓶一样地罩了下来。在那里,我如一只异常温顺的小猫,一声不发,丝毫没有怨恨苍天不公的意思。不知是谁抬了抬我的手臂(也许是亲爱的爸爸吧),我感觉到了,但让我感觉更深刻的,是一种张牙舞爪而来万分张狂的窒息。
明显的,我已没有了气力……
我慢慢松懈开来的手掌心里,没了那几颗浸过毒鼠强花生米(本来是爸爸用来药耗子的,刚才趁他们不备,我吞食了下去)的神奇踪影……
我倒在爸爸的怀中,手脚抽搐,嘴里溢出了鲜血和白沫……
还好,在倒下之前,积蓄所有的力气,被爸爸抓住手臂的我,绽出了一个灿烂无比的笑容,如风雨后的彩虹。
我想,爸爸肯定听到了,那是花开的声音,好美,好动听。那声音袅袅地,带着花香,带着从今往后永远都不会诞生的遗憾,缓缓地、缓缓地遁到天边,遁到七彩云霞的深处,遁到那个欢乐永不退色的极乐世界……